以佛教為代表的外來宗教中國化
來源:中國民族報
時間:2023-02-02 15:05:43
佛教:中國化的同時對中國文化產生深刻影響
佛教傳入中國以后,逐漸融入中國社會,改變了中國人的宗教生活結構。一方面,中國佛教有其本土化的過程,與印度佛教有所不同;另一方面,佛教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,中國文化在歷史上融入了許多佛教元素。有關兩者的互動影響,研究成果很多,譬如著名學者方立天的《中國佛教與傳統文化》,系統討論了佛教與中國政治、倫理、哲學、文學、藝術、民俗等的關系。
兩漢之際佛教的入華,僅有歷史敘事的象征意義。佛教真正意義上的在華傳播,始于佛經的翻譯與解釋。這必須借用中國傳統的思想概念,出現了佛教史上所謂的“格義”。從東漢晚期到東晉末年,經過了250年的佛經翻譯,中國佛教逐漸形成了自成一體的漢語佛教經典系統,并有相應的中國注釋和講經體例,乃至出現“漢語大藏經”,在隋唐時期陸續出現了中國佛教宗派。禪宗、天臺宗、凈土宗、華嚴宗等宗派,無論在理論框架上,還是在修行方法上,都有鮮明的中國特色。佛教在中國的傳播,特別是在民間社會的傳播,大多彰顯出儒家的核心價值。譬如,中國佛教高調宣揚“目連救母”等佛門的孝親故事,到了宋代甚至還有禪師提出“孝為戒先”這樣的口號。
以《隋書·經籍志》為例,略說佛教對中國古代知識體系與精神生活的重要影響。由于大規模的中外文化交流,中國人在隋唐之際的知識體系已有重大變化,集中表現為從《漢書·藝文志》的“六略”過渡到《隋書·經籍志》的“四部二錄”。經史子集的分類法,主要是中國文化自身發展的結果,確立儒家經典的核心地位,把子書當作儒經的附庸,并把數術、方技這些實用知識歸入子書。經歷了魏晉南北朝佛教的大規模傳播,佛教已嵌入到中國人的知識體系里。從中國宗教史的角度來看,《隋書·經籍志》重要之處是在“四部”之后附有道、佛兩錄,構成“四部二錄”的知識體系:經部(十類)、史部(十三類)、子部(十四類)、集部(三類),道經(四類)、佛經(十一類)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術數、方技類的重要性已明顯下降,而整合各類方術并將之納入神靈世界的道經,則在《隋書·經籍志》里得以單列在四部之后。“佛經”部分,展現了中國文化對外來宗教的吸納。更有意思的是,史部、子部還有一些佛教書籍,譬如僧傳、僧人文集。也就是說,這些僧人的生平思想得到了中國主流社會的接納。
若從《隋書·經籍志》所記的圖書篇幅與傳抄數量來看,佛教在當時具有超過儒家經典的廣泛影響力。該書記載當時佛經有1950部、6198卷;道經有377部、1216卷;四部經傳總共3127部、36708卷。佛教文獻體量之大,可見一斑。該書還說,隋代“京師及并州、相州、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,并官寫一切經,置于寺內;而又別寫,藏于秘閣。天下之人,從風而靡,競相景慕,民間佛經,多于六經數十百倍。”由此可見,當時佛教的流傳,已經改變了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與知識結構。
佛教思想與中國本土文化相結合而形成的佛教宗派,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也產生了深刻的影響。儒、釋、道三家在分歧之中相互溝通,到唐代中期,三教合流已成定局,而到明代,這種思想成了中國人的主流意識形態,佛教變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形態之一。不僅如此,這些佛教宗派還傳到朝鮮、日本、越南等地,特別是在唐宋時期促成了中國成為東亞地區的思想文化中心。
佛教在更深層次上的影響,還在于促成了新的風俗習慣。像浴佛節、臘八節等這些民俗節日,都與佛教信仰有關。農歷四月初八是紀念佛陀降生的浴佛節,是佛教最重要的“圣誕節”。臘月八日是紀念釋迦牟尼覺悟成佛的節日,在某種意義上是佛教正式創立的紀念日,中國社會形成了喝臘八粥的習俗,因傳說佛陀在菩提樹下覺悟前接受了牧羊女布施的粥。類似這樣與佛教有關的節日和風俗,還有很多。佛教對民間日常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,其重要原因是佛教有寺院。誠如漢學家許理和所言,佛教傳入中國,不僅意味著某種宗教觀念的傳播,同時還是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形式即僧伽(或譯僧團)的傳入。僧團包括出家人和在家信徒,但以出家人為主導,這使中國出現了專門供僧人修行的道場,即寺院。
除了佛教,中國歷史上還有祆教、摩尼教、景教(也里可溫教)、伊斯蘭教、天主教、印度教、猶太教等外來宗教,它們對中國社會的影響程度不一。國學大師陳垣在1917到1923年間寫就著名的“古教四考”:《元也里可溫教考》《開封一賜樂業教考》《火祆教入中國考》《摩尼教入中國考》,為中國歷史上非主流的外來宗教研究開拓了全新的學術格局。
祆教:隨粟特人皈依佛教后在中國消失
祆教、火祆教,俗稱“拜火教”,即瑣羅亞斯德教,亦稱“馬茲達教”,約在公元前1000年起源于波斯,是古波斯的主流宗教。該教在阿契美尼德王朝(公元前553年-前330年)被列為國教,到薩珊王朝重立祅教為國教,其影響波及中亞地區。現在很多人了解這個宗教,是因為尼采的名著《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》或《蘇魯支語錄》。該教創始人瑣羅亞斯德,又稱“查拉圖斯特拉”,古譯“蘇魯支”。
據專家考證,祆教創立后不久就傳到了中亞錫爾河、阿姆河一帶,約在公元前4世紀左右傳入中國新疆地區。至于傳入中原的時間,專家的意見并不一致,但傾向于西晉末年,即3世紀末4世紀初隨粟特商人傳入。北魏后期及北齊、北周皆有祀胡天的記載,“胡天”即指祆教崇拜的天神。唐高祖時,長安已有祆神廟。到唐武宗會昌滅佛(845年)時,祆教同時被滅。在中國流傳的祆教已非正統的波斯祆教,而是摻雜了許多中亞民俗的祆教,近年在中國陸續出土了祆教徒的墓葬。但總體而言,祆教對中國主流社會的影響不大。
摩尼教:高度佛道教化和民間化
摩尼教,公元3世紀中葉由波斯人摩尼創立,混雜了祆教、猶太教、佛教、景教等的教義而成。這個宗教因為金庸武俠小說出現“明教”而為當代中國人熟悉。摩尼自命為“光明使者”,在得到波斯王沙普爾一世的皈依后,四處傳教。但在這位國王去世以后,摩尼教立即遭到了打壓,波斯境內全面恢復祅教。摩尼本人被捕入獄,相傳后被釘死在十字架上,摩尼教徒只能四處流亡傳教,該教緣此在中亞西域廣泛流傳。
法國人伯希和、沙畹的《摩尼教流行中國考》,陳垣的《摩尼教入中國考》均據《佛祖統紀》卷三十九記載,武則天延載元年(694年)“波斯國人拂多誕持《二宗經》偽教來朝”,認為這是摩尼教入華的最早記錄。這是摩尼教入華的文獻記載,民間傳入的時間還應提前。
該教傳入中國以后,開元二十年(732年),唐玄宗因其“本是邪見,妄稱佛教,誑惑黎元”,即遭禁斷。安史之亂(755年-762年)以后,唐朝請回紇出兵相助,回紇因此把他們的國教摩尼教帶入中原,在唐朝廣為傳播,先后在長安、荊州、洪州、越州、揚州、太原府和河南府等地興建摩尼寺。唐代宗曾給摩尼寺賜額“大云光明”,允許各州設立“大云光明寺”。唐武宗會昌滅佛,摩尼教同時被滅,從此轉入地下,流入民間,漸以“明教”之名流傳于世。如在溫州,宋時有信奉明教的傳統,到元代頗為盛行。在元代東南沿海地區(今福建、浙江兩省),摩尼教還被稱為“蘇鄰國之教”“蘇鄰法”。在福建泉州草庵,至今還有“清凈光明、大力智慧、無上至真、摩尼光佛”的大字石刻。2008年以來,在福建省霞浦縣柏洋鄉上萬村發現大量宋元明清明教文獻和文物。
景教:“廣造奇器異巧”
景教,亦稱大秦教,是早期基督宗教的異端聶斯托利派。景的意思是“大”“光明”,取《新約》光照之義。聶斯托利,古敘利亞人,428年被東羅馬帝國皇帝狄奧多西二世任命為君士坦丁堡宗主教,但他主張耶穌的神性與人性并未合于一位,瑪利亞僅生育耶穌之體,乃純人之母,不能被尊為“圣母”。431年,以弗所宗教大會把他的基督論判為異端,東羅馬皇帝認可這個結論,435年聶斯托利被流放到埃及。他的信徒出逃波斯,得到波斯皇帝卑路斯的保護。約在498年前后,聶斯托利派在波斯成立完全獨立的教會,并由波斯逐漸向東傳教,以至中國。
該教最初被視為“波斯教”,后來更名“大秦教”。《唐會要》卷四十九“大秦寺”條記載:“天寶四載九月,詔曰:波斯經教,出自大秦,傳習而來,久行中國。爰初建寺,因以為名。將欲示人,必修其本。其兩京波斯寺,宜改為大秦寺;天下諸府郡置者,亦準此。”該教入華的歷史研究,得益于約明代天啟五年(1625年)在西安出土的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”。據碑文記載,唐貞觀九年(635年),阿羅本來到長安,唐太宗命房玄齡接待,并在京師建造大秦寺。
景教隨商貿活動經由西域“絲綢之路”傳入中國。歷史上景教徒多擅經商,這也是他們與明清之際天主教會顯著不同的地方。景教徒的傳道方法類似后來的耶穌會士,他們往往擁有豐富的天文學知識,借助希臘的醫學醫術,并有實際的治療效果;同時“廣造奇器異巧”,引起中國人的興趣。唐武宗會昌滅佛時,殃及了景教。不過,景教一直在中亞一帶流傳。元朝對景教采取懷柔政策,其得以興盛,但已改稱“也里可溫教”。
元代景教極盛之后歸于衰亡,直到明末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入華,基督宗教才再次進入中國。
伊斯蘭教:全方位進行中國化的調整
伊斯蘭教,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同的稱呼,唐宋時稱“大食法”,元代稱“回回教門”,明代又稱“天方教”“回回教”,明清之際稱“清真教”,清代以后稱“回教”。該教以《古蘭經》為根本經典,由穆罕默德于610年創立。有關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內地的時間,有多種說法,現大多采納唐永徽二年(651年)傳入的說法。伊斯蘭教傳入中國,主要有兩條路線:一條由中亞傳入天山南路,逐漸傳入中國北方,在甘肅、西安一帶設立寺宇;另一條由大食從海路傳入中國南方,在廣州及沿海地區建立寺宇。在元代已有“回回遍天下”的說法,當時的伊斯蘭教制度發生新的變化,由唐宋時期的“番坊制”,發展成為較完善的“三掌教制”。清真寺設三種不同的職務,教長(協調清真寺所有事務)、贊教(協助教長工作)、宣教(負責召喚穆斯林到清真寺按時禮拜),初步完成了從外來宗教到本土化宗教的轉化過程。明代朝廷對伊斯蘭教的政策較為包容,明末清初有一批穆斯林學者積極探索伊斯蘭教的中國化,北方興起經堂教育,南方則以南京、蘇州為中心,出現了以王岱輿、劉智為代表的“以儒詮經”,形成現在所說的“回儒”,主張“二元忠誠”,既忠于真主又忠于君王。這標志著伊斯蘭教從制度、教義到教育方式都進行了中國化的調整。
猶太教與印度教
作為基督宗教和伊斯蘭教源頭的猶太教,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傳播,但影響很小。陳垣《開封一賜樂業教考》推測,猶太教可能在唐代已經入華。不過,在他看來,開封猶太族非宋以前所至;猶太族之見于漢文記載者,莫先于《元史》;“一賜樂業”之名,起于明中葉。
作為印度的主流宗教,印度教在中國的影響遠不能與佛教相比,但也有不少的影響。印度教在中國建廟,始見于《唐大和上東征傳》。唐天寶九年(750年),鑒真發現廣州“有婆羅門寺三所,并梵僧居住……江中有婆羅門、波斯、昆侖等舶,不知其數;并載香藥、珍寶,積載如山。”著名學者黃心川的《印度教與中國文化》介紹了印度教傳入中國的四條路線(絲綢之路、海上絲綢之路、滇緬山路、尼泊爾山路),梳理了中國保存婆羅門教或印度教的史料和文物,認為印度教對道教、瑜伽術對氣功都有一定的影響。
從以上這些外來宗教的經歷來看,凡能像佛教那樣經歷“華化”或“中國化”,就相對容易在中國扎根,否則難以存活,至少很難有影響。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,與其主動進行中國化的努力密不可分。中國文化講究“和而不同”,相信“殊途同歸”,喜歡不同文化的相互包容,而不喜歡以一種文化替代另一種文化。中國社會接受外來宗教的前提,是外來宗教能認同中國的本土文化。
(本文作者:李四龍,文章來源:中國民族報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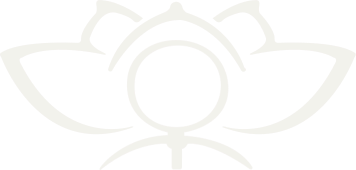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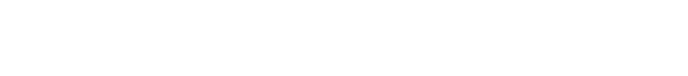
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8566號
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8566號